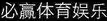bwin官网因此,最终我们考虑的变量为被调查者的工资收入( y ,单位:人民币元) 、 接受教育的年数( x1 ,单位:年) 、性别( x2 ) 、是否属于东部地区( x3 ) 、工龄 ( x4 ,单位:年)等。表 1 给出了对所用数据的简单统计描述。
王明进 岳昌君∗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北京 100871)
二、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1991 年、1995 年、2000 年以及 2004 年的 中国城市住户调查数据。 由于每年的原始数据中包含了个别明显的错误以及变量 的含义也不尽相同,因此,我们事先对数据进行了如下的一些处理: (1)去除了数据中明显的不合理的观测,包括性别、学历、就业、省份等 不在正确的编码范围内的情况; (2)去除工龄不到 1 年(即 0 年)以及年龄不满 16 岁或超过 70 岁的观测; (3)对于 1991 年的数据,采用的工资收入水平为“收入总计”减去“财产 性收入” (含利息、红利和其它财产租金收入)“转移性收入” 、 (含赡养收入、离 退休金、价格补贴和其它转移收入)和“特别收入” (含赠送收入、亲友搭伙费、 记帐补贴、出售财物收入和其它特别收入) ; (4)由于得到的 1995 年数据中没有包含性别变量,因此对 95 年数据的分 析没有考虑性别因素;另外,我们得到的 95 年的数据中被调查者的最低收入为 1003 元,显然是被截取过的数据,因此对分析结果的解读会有一定的影响; (5)对于 2000 年的数据,由于没有更细致的信息,工资收入水平按照被调 查者的“收入总计”来计算; (6)对于 2004 年的数据,工资收入水平按照被调查者的“工薪收入”计算; (7)去除全部数据中工资收入为零的观测; (8)按照被调查者的最高学历对其接受正规教育的年数做了如下处理:研 究生学历记为 18.5 年,大学本科学历为 15.5 年,大学专科为 14.5 年,中专和 高中学历均记为 11.5 年,初中学历为 8.5 年,小学学历为 5.5 年,其它未上学 或者只进过扫盲班的为 0 年。1991 年到 2000 年的原始调查数据中没有考虑研究 生学历,因此最高学历是大学本科;而且 1991 年的数据中没有区分大学本科和 大学专科学历,因此都按 15.5 年计。 (9)为了考虑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异,对全部数据,按照被调 查者是否属于东部地区进行了划分,即所在省份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 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划为东部地区。
[2] 增加一年的教育个人的收入平均仅仅增加 1.4%。 毛瑞法兹欧 (1999) 基于 1988
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调查的数据,发现明瑟教育收益率只有 2.9%。[3] 然而,一些研究发现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的教育收益率有上升的趋势。 张俊生和赵耀辉(2002)使用包括 6 个省市 1988-1999 年的城调队数据,研究表 明我国的个人教育收益率从 4.7%逐年上升至 11.7%。[4] 李海政(2003)使用的 是 1995 年 11 个省市的城镇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得出的我国个人教育收益率是 5.4%。[5]陈晓宇等(2003)使用包含 30 个省市区的 1991 年、1995 年和 2000 年 的城调队数据,利用简单明瑟收入方程进行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的个人教 育收益率从 1991 年的 6.8%上升到 2000 年的 8.5%。[6]李实和丁赛(2003)使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和城镇贫困研究课题组的两次住户 抽样调查数据,发现教育收益率在 1990-1999 年期间是逐年上升的,简单明瑟回 归方程的结果显示教育收益率从 1990 年的 2.4%上升至 1999 年的 8.1%。
教育作为一项人力资本投资其收益是多方面的,不仅体现在受教育者个人文 化素质、道德修养、生活技能的提高,也表现为受教育者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 从而提升受教育者本人及其亲属的生活质量。前者称为教育的非货币收益,后者 则是货币收益。在对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的研究中,由于很难对非货币收益进行计 量, 人们通常只考虑受教育者因接受教育而带来的收入变化, 因此仅是货币收益。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劳动者的 收入水平。实践中,由于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经济制度不同,经济发 展水平不同,因此教育的收益率存在较大的差距。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基于 明瑟收入函数的实证研究方法(Mincer,1974) ,几乎所有的文献都发现我国从 改革开放以来到 90 年代初期的教育收益率都很低。[1]例如,白瑞安和马Βιβλιοθήκη Baidu拉托 (1990)使用 1986 年对 800 名南京市国有企业职工的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教育机会与收入不平等研究” (05JJD880052)的成果 之一。感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陈良焜教授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 ∗ 作者简介 王明进(1970-) ,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岳昌君(1966-) ,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
一般说来,教育收益率呈现显著上升的趋势,人们对教育的需求就会显著增 加。然而,近几年来不同群体对教育需求并没有表现出一致的增加。尽管大多数 人对较高层次的教育有着越来越强烈的需求,但是,某些群体开始主动放弃本可 获得的教育机会,表现出对教育需求的不足。例如,一些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在 家庭的干预下主动辍学,很多初中毕业生选择不上高中,一些高中毕业生主动放
弃高考,数以万计的高考考生拿到录取通知书却不报到。之所以出现这种看似矛 盾的现象,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有教育成本上升、 教学内容脱离实践等原因, 另一方面, 对未来能否成功找到满意的工作并获得期望收益的担心也是学生弃学 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与其他投资形式一样,教育投资也存在某种程度的风险。然而,在 教育经济学的文献中,有关教育投资收益的研究很多,对教育投资风险的计量和 分析却很少。贝克尔(1985)是最早对教育投资风险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之一。 在《人力资本》一书中,贝克尔对教育投资风险的含义进行了解释:“人力资本 的实际收益围绕着预期收益变动,这是因为某些因素的不确定性。一个年龄与能 力既定的人的收益也是不确定的,因为还有许多无法预料的事情。”[8]此后,其 他学者对此问题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尽管迄今为止对何谓风险还没有一个统一 的认识,但毋庸置疑风险与不确定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本研究中的个人教育投资风险指的就是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按照 前面的划分,这种不确定性既可以体现在非货币收益上,也可以体现在货币收益 上。类似地,我们也可以分别把它们称为教育投资的非货币风险和货币风险。同 样地由于对前者计量的困难, 我们这里把个人教育投资的风险局限在后者即受教 育者收入变化的不确定性上。举例来说,一个接受了四年大学本科教育的人,他 的教育投资的收益是他现在得到的收入与假定他没有接受这四年教育时他应得 的预期收入的差值,而他的教育投资的风险则体现在这一差值是不确定的。如果 这一差值低于了它的平均水平,显然单纯就增加的收入来说,这个人接受的四年 大学教育是不成功的。基于此,我们可以用刻画这一收入差值的变异程度的一些 量来度量这个人大学四年教育投资的风险。 显然,没有理由认为不同个体的教育投资风险是相同的。然而在目前大量文 献的实证研究中, 无论是估计教育投资的绝对收益还是相对收益所采用的模型事 实上都假设了教育风险的齐性,即不同人的风险是一样的(具体见后面第二节的 分析) 。本文的贡献体现在:在明瑟收入方程的基础上,改变随机扰动项同方差 的假定,认为不同人的风险是不一样的,采用新的计量回归模型对教育投资风险 进行估算。 本研究对教育投资风险所采用的计量指标和结果与人们通常对风险的 直观理解是一致的。风险的大小意味着预期收益的波动程度。实证研究结果对人